認為伊斯蘭=野蠻落後,說明你實在太無知
關於宗教極端化和“伊斯蘭恐懼症”的思考
作者按
2017年8月15—16日,由我國外交部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處聯合主辦的“第七屆中阿關係暨中阿文明對話研討會·中阿文明對話暨去極端化圓桌會議”在成都舉行。包括埃及大穆夫提等阿拉伯世界頂級宗教人士在內的70多位中阿官員、宗教界人士、學者出席了會議。北京外國語大學薛慶國教授也參加了此次會議,並用阿拉伯語做了“關於宗教極端化和‘伊斯蘭恐懼症’的思考”的發言。由於時間所限,演講內容在此稿基礎上有所刪減和改動。經薛慶國教授授權,活字文化特發表由他本人翻譯的演講中文稿,希望有助於讀者增進對有關議題的瞭解。感謝薛慶國教授對活字文化的支持!

論壇現場
毫無疑問,伊斯蘭教是偉大的宗教。在《古蘭經》、聖訓等伊斯蘭經典中有許多教誨,敦促穆斯林遵行中正、寬容、平等、和平、正義、誠信等崇高的價值觀。伊斯蘭歷史也不乏體現了這些教誨和價值觀的史實和事件。正是由於這些教導和實踐,中世紀的穆斯林才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文明,全人類至今仍然從其文明成果中受益。
作為一位從事阿拉伯語言、文化的研究、翻譯、教學工作已有30多年的學者,我深知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博大精深和輝煌歷史,同時也瞭解這一文明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及眾多問題。和與會的來自阿拉伯世界和我國的宗教界領袖和學者一樣,我也堅決支持對宗教極端化說“不”,對“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說“不”。

薛慶國教授(中)
左右分別為突尼斯前宗教部長和阿曼宗教學者
與此同時,我認為看待任何一門宗教——伊斯蘭教也不例外,既要閱讀經典和教義,也要看廣大信徒的實踐。因此,要在世人面前傳達伊斯蘭教光輝、文明、進步的形象,一條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將穆斯林社會建設成為體現光輝、文明、進步特徵的社會;而極端、封閉、落後、紛爭等等消極現象,則不僅有悖於伊斯蘭的價值觀,而且也助長了“伊斯蘭恐懼症”在各地的蔓延。
談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情況,首先,我想援引一下在現代中國傳播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文化最傑出的兩位先驅者的言論,他們兩人都是穆斯林學者,都曾于上世紀初在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9年,其中之一是我的老師、研究阿拉伯歷史文化的著名學者納忠教授。在1929年創刊的穆斯林刊物《清真鐸報》上,青年納忠發表了《鐸報應負之使命》一文,其中指出了中國回民面臨的當務之急:“改良回民教育,促進回民之宗教觀念,灌輸宗教知識,介紹世界新思潮,使之有穩定之主見,作堅決之信仰,具世界之眼光,作遠大之事業。”

納忠教授(1909-2008)
他還清醒意識到,落後保守的東方伊斯蘭社會與進取開放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著巨大差距:
“論思想,彼則積極圖謀外張;我則隨事皆主保守。論教育,彼則取法從新,力謀改革,而適應環境個性;我則因襲傳統,死守絕望,而反逆潮流,摧殘個性。論學術,彼則順時代之呼聲,循文化之需求,研究科學,發明物理;我則口不離念禮齋課,手不離五大冊本,潮流時代皆不問也。嗚呼!念禮齋課,固伊斯蘭教中最重要之主命,而當然遵踐之事務也。然此乃個人之私刑問題,非伊斯蘭教之經義僅此也。”
我援引的第二段文字,出自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古蘭經》最權威的漢譯本譯者馬堅先生之手。1934年,馬堅先生曾在開羅作過一次介紹中國伊斯蘭教的演講,其中指出中國穆斯林落後的原因有:“愚昧無知,內部不團結和生活的貧困。”關於愚昧無知,馬堅認為包括兩層含義:
“一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代科學知識缺乏應有的瞭解,以至於有些穆斯林宗教學者還是漢文盲,不能用漢語閱讀和寫作,甚至個別人還認為學習和掌握漢語文化及科學知識,會影響到宗教信仰,因而寧願自己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二是對伊斯蘭教缺乏全面的理解,以至為宗教的細枝末節爭論不休。”

馬堅教授(1906-1978)
馬堅先生在演講中列舉了10個最明顯的例子,包括為死者做祈禱時是否要脫鞋,穆斯林是否必須留鬍子,穆斯林婦女能否剪髮,穆斯林是否可以做豬鬃生意等等。在馬堅看來,這些問題都是無足輕重的,但由於無知,這些問題在部分中國穆斯林中間引起紛爭和不和,有時甚至造成相互間的敵意和仇殺。
這是八、九十年前中國穆斯林的情況,那麼今天的情形如何?無疑,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穆斯林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也還存在不少挑戰。回族學者李振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馬堅傳》中認為:“馬堅60多年前談到中國穆斯林對文化教育不重視的情況,談到宗教內部由於枝節問題產生嚴重分歧的情況,就好像在說今天的事情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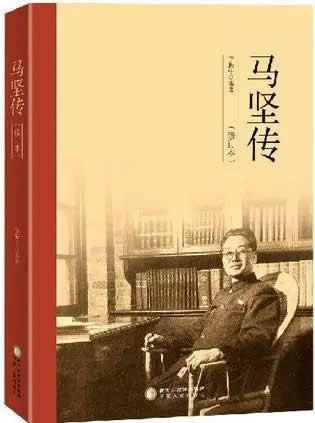
在我看來,中國的伊斯蘭教發展目前主要面臨兩個挑戰,或許,這也是伊斯蘭教在全世界面臨的挑戰。一是近年來“伊斯蘭恐懼症”在中國社會也有一定市場,部分民眾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存在誤解和偏見,這是令人遺憾和不安的,因為這不僅傷害了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感情,而且妨礙了各民族間的團結與和諧,甚至為社會穩定造成了隱患,需要我們果斷地通過思想、文化、傳媒等各種手段予以應對。
第二個挑戰表現為部分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真諦的理解有失偏頗,與偉大的宗教及其燦爛的歷史並不相稱。除了馬堅和納忠兩位先賢指出的問題之外,近年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譬如,在部分穆斯林聚居區,尤其是在南疆部分地區,黑色面紗和罩袍成了女性乃至未成年女孩的流行服飾,泛化“清真”、過分區分“清真”、“非清真”的現象一度頗為嚴重,以至於飲用水、書寫用紙、皮鞋、牙刷牙膏等物品也都有“清真”與“非清真”之別。收聽或收看政府的廣播與電視,音樂與歌唱,婚禮上的舞蹈,葬禮上的哀哭,乃至政府用來扶貧的各類電器,也都被打上了“非清真”的標籤。
於是,以海納百川成就偉業的伊斯蘭教形象被曲解成封閉僵化的形象,宗教的寬容為本被曲解成偏執和狹隘,中正被曲解成極端,方便易行的宗教被曲解成繁瑣艱難的宗教,一個在所有科學領域都曾有過重要創造的、注重人道的文明,被曲解成鬍鬚、面罩、服飾等雞毛蒜皮的枝節。
也許有人會說,這些問題是體現穆斯林身份的生活方式與宗教自由問題,與政治無關,所以不應該被視為極端。這種看法顯然值得商榷。當今伊斯蘭世界生活方式最保守、最偏執的地區,難道不是塔利班、基地組織、達伊什、博庫聖地等極端組織曾經或依然控制的地區?沙特著名作家圖爾基·哈麥德曾以“9·11”事件劫機者群體為主人公,寫過長篇小說《天堂之風》,旨在探討導致年輕人走上極端與恐怖之路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背景。主人公之一阿卜杜勒·阿齊茲成長於利雅德以西的一個小鎮,他從小就被告知,穆斯林不能聽音樂、開玩笑,不能跟妻子以外的女性有任何接觸。在他經常去禮拜的那個清真寺裡,伊瑪目“從不使用先知及其弟子們沒有使用過的任何物品”,因此不用電器,不用印滿“非法”圖案的紙幣,出門只騎毛驢,穿的衣服是自己在家縫製的,生病了也絕不用西藥,甚至他供職的小清真寺也是親手用泥土壘砌,其中沒有任何現代設施。

Turki al-Hamad,沙烏地阿拉伯當代著名小說家、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多次呼籲政教分離等自由主義主張,曾被沙特政府拘捕入獄(據外網整理)
這種與世隔絕、“純潔”得令人匪夷所思的生活場景,顯然反映了某種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這一場景,與伊斯蘭文明公認的黃金時期阿拔斯王朝的生活場景形成了鮮明對照。現代埃及學術大師艾哈邁德·愛敏在巨著《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中,是這樣描述阿拔斯文明的:
“阿拔斯文明像一切文明一樣,包羅萬象:既有清真寺,也有酒館;既有誦經者,也有行樂者;既有深夜禮拜者,也有在花園用早點者;既有富得腰纏萬貫者,也有窮得不文一名者;既有對宗教懷疑者,也有虔誠信教者。而徹夜不眠的人,有的是虔誠禮拜的,有的是尋歡作樂的。所有這一切都斑駁陸離地出現在阿拔斯時代。”

鼎盛時期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
西元751年(盛唐天寶十年),阿拔斯王朝軍隊與唐安西大都護高仙芝在今哈薩克斯坦地區爆發著名的“怛羅斯之戰”,唐軍一潰千里、大敗而逃。史學界通常認為,從此中原王朝基本上喪失了對中亞地區的控制權。
由此可見,生活方式還反映了文明的興衰,兩者之間有著互為因果的邏輯聯繫。一個正常的人間社會,必定是豐富多彩而充滿活力的;而一個佈滿禁忌的社會,不僅難以維繫,而且只會扼殺文明創造的活力,最終釀成悲劇。
又譬如,部分中國穆斯林僅僅從“宗教”層面理解伊斯蘭,把它理解為教法學家、經注學家筆下的律令,而非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文明。他們對古今伊斯蘭世界燦若群星、彪炳史冊的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蘇非主義者的精神成就的深度、廣度所知甚少。有些人受到賽義德·庫特布、毛杜迪等原教旨主義理論家的影響,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視“思想”、“理性”、“創新”為畏途、異端乃至大逆不道,一味強調回歸過去,回歸經訓,而忽視了從總體上把握宗教經典的精髓,並對其做出合乎時代要求的解讀。然而,無視宗教經典降示的複雜背景,對經典文本作斷章取義的教條式解讀,會導致十分嚴重的後果。在當今世界蔓延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就是其後果之一。我在此補充一個中國歷史上與此相關的故事,據《多桑蒙古史》記載:
“《可蘭經》有雲:‘凡崇拜數神者,殺之。’基督教徒曾在帝(即元始祖忽必烈)前引此語。帝聞之,召都城之回教博士至,而詢其為首者:彼等聖經中是否有此語。諸人不能否認,對曰:有之。忽必烈曰:汝曹以《可蘭經》授自上帝歟?其人對曰:吾曹未嘗致疑也。可汗又曰:上帝既命汝曹殺異教之人,何以汝曹不從其命?對曰:時未至,吾曹尚未能為之。帝怒曰:然則我能殺汝也。遂命立將其人處死。”

在《古蘭經》中,固然有“殺戮”、“俘虜”、“圍攻”異教徒和“以物配主者”的說法,但那都是有一定前提的,且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目的。在其他宗教的經典中,也不乏類似的內容。總體而言,伊斯蘭教絕不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戮異己,《古蘭經》中還有大量宣導和平和寬容的經文。顯然,忽必烈面前的那位“回教博士”對宗教的理解片面而膚淺,結果遭致殺身之禍。可見,對宗教經典作與時俱進的再闡釋,是一項勢在必行的工作。
最後,我還想再談談“伊斯蘭恐懼症”話題。在部分對伊斯蘭文明知之甚少的民眾眼裡,伊斯蘭成了落後、封閉、偏執的代名詞,又常常與暴力、恐怖等惡性事件有關,因此,它是值得擔心和恐懼的。
但是在我心目中,卻有著一個絕然不同的伊斯蘭形象。從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魯世德、伊本·赫勒敦、伊本·阿拉比等古代哲學家的筆下,從穆太奈比、麥阿裡、伊本·穆格法等古代文學大師的筆下,從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篤、塔赫塔維、艾哈邁德·愛敏、紮基·馬哈茂德、穆罕默德·阿爾昆、阿比德·賈比裡、哈桑·哈乃菲等近現代思想家的筆下,從紀伯倫、塔哈·侯賽因、努埃曼、馬哈福茲、黑托尼、達爾維什、阿多尼斯、賽阿達維等等我十分熟悉、並有幸見過、乃至結識其中部分人的現當代文學大師的筆下,甚至,從我十分敬重的霍達、張承志、沙葉新等回族作家的筆下,從我的穆斯林師長納忠、馬堅、劉麟瑞等前輩的著作和教導中,我瞭解了這樣的一個伊斯蘭——
它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明體系,兼顧精神與物質、個人與集體、理想與現實、權利與義務,追求“兩世吉慶”,注重道德理想,留下了豐碩和寶貴的文明成果。穆斯林乃至人類在此生的使命,不是恪守繁文縟節和清規戒律,不是只念來世而逃避今生,甚至不僅僅是敬畏和贊念至高無上的真主,而是履行真主賦予的“代治者”使命,即代替造物主治理好世界,將大地改造成人間的“真境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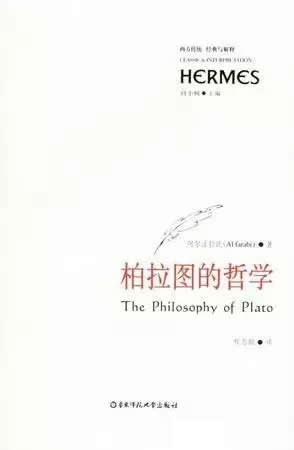
在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中,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古代文明典籍亡佚一空,學者只知其名、不知其書,而是阿拉伯人保留下了這些古代經典,並“外轉內銷”地再傳回歐洲,從而才有了經院哲學的興起和隨後的文藝復興。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阿拉伯哲學家阿爾法拉比。
按照這樣的伊斯蘭理解,穆斯林的身份不是定格於過去,或拘泥於形式,而是勇往直前,在各個領域勇於創造和創新,無所畏懼地擁抱時代和未來。因為只有這樣,穆斯林才不會淪落為人類歷史的被邊緣者、落伍者乃至犧牲品,而會像伊斯蘭文明輝煌時期的前輩那樣,成為文明構建的領先者、推動者、參與者。在人類發展面臨諸多困境和危機的今天,伊斯蘭文明以其獨特而豐富的精神資源,還有理由成為人類文明進程的糾偏者。
這樣的伊斯蘭,不會是世界人民“恐懼”的物件,而必將是世界文明大花園中,一株光彩奪目、馨香沁人的鮮花。
感謝流覽伊斯蘭之光網站,歡迎轉載並注明出處。

 古蘭經漢譯查詢
古蘭經漢譯查詢 穆斯林手冊
穆斯林手冊 古蘭經分類查詢
古蘭經分類查詢 禮拜時間(刻)查詢
禮拜時間(刻)查詢 古蘭經語音查詢
古蘭經語音查詢 電子版中文古蘭經
電子版中文古蘭經











